从难民营赶到前线的巴德,第一时间来见温特斯:“特尔敦人要投降?”“是。”温特斯俯在图纸上勾画,左手拿起水囊递给巴德,头也不抬地回答:“我没同意。”战友之间不需要寒暄和客套。巴德接过水囊,呷了一口清水,静静等待温特斯的下文。温特斯丢掉炭笔,叫来传令兵拿走地图。临时指挥所内再没其他人,他也就不需要再隐藏倦意。他走向帐篷角落的水桶,用冷水使劲洗了把脸:“烤火者称愿意归还所有掠获,献上三千匹马,就此罢兵——保留武器、旗帜,体面地投降。哼,赫德人也开始玩这一套了!”临时指挥所设在一处能俯瞰东南方向的高地上,从这里能看到第三道防线,以及更远处的森林。不时有传令兵策马而来,用口信的方式向温特斯汇报,又带上答复匆忙离去。“特尔敦人没有动作?”巴德俯瞰地图,研判着两军态势。温特斯微微摇头,眉心不自觉皱起:“没有动作……所以我有些想不明白猴屁股脸在搞什么鬼。”当下特尔敦右翼已经被分割成三部分:一部分在大角河西岸,在之前的战斗中被击退;一部分在滂沱河南岸,也就是下铁峰郡;汗帐精锐则被困在大角河、滂沱河以及第三道防线围城的方寸之地。形势对于铁峰郡军来说一片大好,只要能围歼汗帐精锐,剩下的乌合之众将不战自溃。“就算是兔子掉进陷阱,也要垂死挣扎一番。猴屁股脸被困在死地里,反倒请降示弱。”温特斯向巴德说出心中的疑惑:“假设是猴屁股脸处在我的位置,你觉得他会接受他开出的条件吗?”“不会。”巴德顺着温特斯的话往下说,帮助温特斯理清思路。“也就是说。”温特斯无意识摆弄着一柄小刀:“猴屁股脸在做一件他明知不会成功的事。”巴德稍加思索:“烤火者另有目的?”“必然是这样。”“拖延时间?”“为什么?”温特斯将桌面的几滴水气化,以此刺激精神:“时间拖得越久,墙就越高、壕沟就越深,特尔敦人面对的防线就越坚固。”“或许是想先示弱麻痹我们,然后再卯足力气打穿防线。”“可是依我看,以特尔敦人的骑兵优势,不如以快打快,抢在墙壕体系尚未构筑完善前突击……”话音戛然而止,温特斯蓦地沉默。片刻之后,他轻轻开口:“要么,特尔敦人在等待援军里应外合,把我们歼灭在这里。”巴德没有接话,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打断温特斯。温特斯陷入冥思苦想,他双手撑住桌面,紧紧盯着地图:“援军……援军……如果特尔敦人有援军,援军又从哪里来?西岸?南岸?北面?”巴德叹了口气,拍了拍温特斯的肩膀。温特斯回过神来,茫然望向好友。“你多久没睡觉了?”巴德问。“一天?两天?”温特斯的眼睛里满是血丝:“好像小睡过几次,我也记不清了。”“这样不行。”巴德的神色愈发严肃:“第二诫,[为将者心力交瘁、筋疲力尽]。”温特斯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笑意,对暗号似地答出下一句:“[就会忽视真正重要的事情]。”“睡觉去吧。”巴德把大衣递给温特斯:“我守着这里。”温特斯本要说什么,转念一想,抱起大衣走向帐篷里间。他打定主意说道:“总之以不变应万变。不管特尔敦人在搞什么鬼,只要口子扎紧,就赶特尔敦人出来!”巴德望着温特斯的背影,又环顾指挥所,眼神有些复杂。这座指挥所只有四顶帐篷,可谓简陋至极。但是此时此刻,它发布的命令调度着上万人的行动,做出的决策关乎铁峰郡的生死。毫不夸张地说,这四顶帐篷就是铁峰郡军的大脑和核心。可它却面临着严重的人力短缺:能读会写的文员两只手就能数出来,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除了温特斯和巴德更是一个没有。之所以铁峰郡军队尚能正常运转、没出大乱子,完全是因为所有东西都装在温特斯的脑海中,凭着温特斯的脑力在计算。“这样下去不行。”巴德蓦地开口:“你需要助手。”“你不是来了吗?”温特斯展开行军床,慢悠悠回答。“很多助手,很多很多助手。”“是啊。”温特斯重重躺下,很快就睡着了。而巴德拿起纸笔,凭借记忆开始撰写一份名单。……中铁峰郡,第三道防线。四名壮实农夫正在使用一台打桩机。四人喊着号子扳动转轮,明明已是寒风凛冽的冬季,他们却干得汗流浃背。转轮的轴上缠着粗大绳索,绳索另一端系着一块大石。转轮收紧绳索,大石也被缓缓拉起。石头被抬升一段距离之后,农夫们砸开卡笋。大石猛地下坠,重重砸在木桩上。这个过程不断重复,只用了六七下,便将一根四米长的原木打进地里,地上只露出两米左右的木桩。木桩打好,农夫们便不再管它。另有一些农夫走到打桩机旁边,十几人齐心协力把这架简陋的机械搬动两步。然后换上另一组农夫,开始打另一根木桩。西南方向,一座山坡的背后,泰赤窥视着远处简陋但是高效的机械,脸色发青。在他目光所及之处,至少有八架打桩机正在同时施工。一根一根木桩打下来,山谷里已经树起一连串间距两步左右的“木桩墙”。巴德的到来给了温特斯短暂的休息时间,与此同时,泰赤则带领亲卫穿越森林,抵近探查敌情。在三百步的距离上,泰赤终于看清对方是如何“一夜筑城”:先打木桩,之后将柳筐似的东西套在木桩上;在木桩前方取土,往柳筐里填;一个筐填满土,再套上另一个新筐;如同木签串肉,木桩一连被套上六个筐;前四个筐先套再填土,后两个筐先填土再套;木桩之间的宽大空隙被装满土的柳筐填充,两腿人再将浮土盖在墙体外面,使其浑然一体,看不出里面的奥妙;最终,土墙竣工,取土挖出的坑也就成了壕沟。“看懂了吗?”泰赤咬着牙问儿子。“看懂了,那木桩子是脊骨,柳筐是肋骨,泥土是血肉皮囊。”泰赤的儿子舔着嘴唇回答:“要想拆这墙,只能拖倒木桩。木桩一倒,墙也就跟着倒了。”“那木桩入地至少三步深,如何拖得倒?”泰赤瞪起眼睛。泰赤的儿子也瞪起眼睛,神情与父亲如出一辙:“一匹马拽不倒就用两匹,两匹马拽不倒就用四匹。”泰赤看着儿子的模样,苦叹了一声:“怕是两腿人盼着你我如此来呀。”……筑墙的建材无非是泥土、木材和石头。以千秋万代计,最好使用石头,即石灰砂浆或是火山灰砂浆。但是温特斯并非要修教堂,他要修的是野战工事,速度才是关键。他的选择只剩下土和木头。木头筑墙最简便,原木一根紧挨着一根打进土里就是墙。然而这种方式需要数以十万计的木材,温特斯没有。他的选择只剩下土。泥土的问题在于不牢固,会发生滑动。如果只是单纯将土堆起来,土堆将自然形成一个坡度。所谓的“六尺墙角八尺壕,正墙要满七尺高”便是这个缘故。只是坡度如果太大,就失去了阻拦战马的意义。因此自古以来以土筑墙,最关键的技术在于“束土”。夯土是一个办法,可惜还是不够快。用羊皮囊和麻布袋盛土垒墙是最理想的方式,可惜温特斯既缺少羊皮囊,也缺少麻布袋。什么都没有,就只能因陋就简、因地制宜、有什么用什么。苦思之下,温特斯另辟蹊径,改进了沃邦中校在赤硫岛上修筑甬道的工程方式。赤硫岛甬道是“以笼束土”,温特斯则“以筐束土”。因为筐的结构强度不如笼子,而且难以像笼子那样整整齐齐堆叠。所以温特斯在筐结构的基础上,额外打入一根木桩作为“主心骨”。既是增加墙体的强度,同时也能将土筐牢牢固定住。这种强度的“墙”,抵挡炮击可能有些强人所难,但是拦住战马没有任何问题。比起普通垒土墙,以筐束土能将墙体修得更陡峭,使战马连借力的地方也寻不到。而且不挑建材,烂泥碎石都可以用。修筑效率比羊皮囊、麻布袋束土慢,可远比夯土、砂浆等方式快。……泰赤望墙兴叹的时候,另一边的温特斯忽然从睡梦中惊醒。温特斯的身体忽地直直坐起,他怔怔盯着帐篷的蒙布,动也不动。巴德听到声响,走进里间帐篷:“怎么了?”“我梦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”温特斯回答。巴德吃惊地看到温特斯的额头沁出冷汗。温特斯甩到大衣,一跃而起,冲着帐篷外面大吼:“给我备马!召集所有连级指挥官!”小小的指挥所顿时一阵骚乱。“怎么了?”向来沉稳的巴德看到温特斯的模样,也有些惊诧莫名。“我可能知道特尔敦人要干什么了。”温特斯紧紧攥住巴德的胳膊:“不能再拖了!要快!”手机站全新改版升级地址:https://wap.ibiquges.com,数据和书签与电脑站同步,无广告清新阅读!
 爱心猫粮1金币
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
南瓜喵1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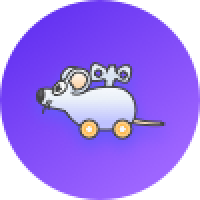 喵喵玩具50金币
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
喵喵毛线88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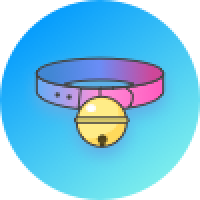 喵喵项圈100金币
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
喵喵手纸200金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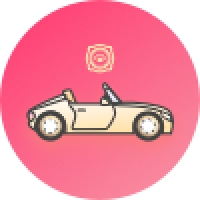 喵喵跑车520金币
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
喵喵别墅1314金币

